身份套利規避監管:SHEIN在地緣政治上走鋼絲快訊
如海外輿論場尤其關注的希音全球官網中的企業介紹部分,已經找不到“China”,而是以“global”替代。

SHEIN(以下稱“希音”)可謂是一家既神秘又聲名鵲起的公司,我們固然知道這是一家緣起于中國的全球線上快消企業,成長性也令市場咋舌(估值已經超過H&M 和Zara總和),但當我們檢索企業相關信息時,不僅發現創始人許仰天公開信息非常至少,且企業在相關問題的表述上又含糊不清。
如海外輿論場尤其關注的希音全球官網中的企業介紹部分,已經找不到“China”,而是以“global”替代。顯然,在業務發展中希音首先陷入了身份焦慮,一方面其確實在享受中國制造的低成本和高效紅利(番禺供應鏈總部可謂中國制造熱土),但另一方面在地緣政治壓力之下,希音又覺得中國標簽反而成了一個包袱,在對外表述實際行動中又要盡量規避這一身份。
這些都勾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本文我們就從擰巴的身份對希音展開分析,來探求其背后的原因,核心觀點:
其一,當前 “既要,又要”的身份定位確實有利于短期利益利益最大化,但長期內看這無異于在敏感的地緣政治中走鋼絲,風險非常之大;
其二,善舞長袖在初期確實是企業發展的有利要素,只是在當前的環境下,這很容易引起社會和輿論的反感,近期富士康在我國的一些爭議也應該引起希音的警惕;
其三,IPO之后公司成為公共公司,隨著信息披露制度的健全,希音恐將面臨輿論場沖擊。
身份焦慮起源:IPO和財富保值
我們首先盤點了希音近期有關身份焦慮的一些行為:
1)越發強調自己是一家全球公司,淡化中國企業身份,公司總部已經搬往新加坡,許仰天最早成立的的南京點唯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已經注銷,由此希音完成了身份的轉化;
2)根據路透社披露,許仰天已經成為了新加坡永久居民(本人尚未公開承認,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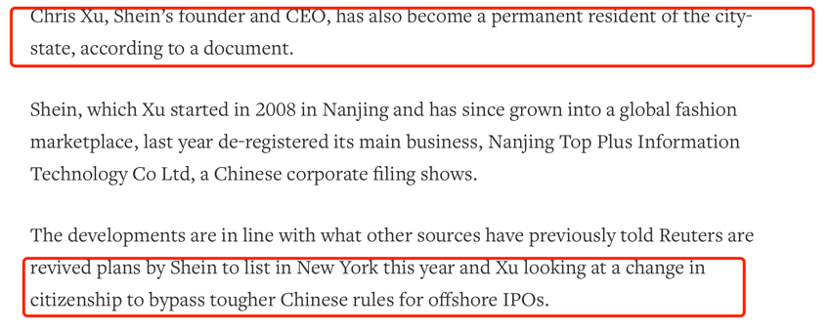
3)希音供應鏈主要依托于中國,在廣東番禺城中村密布著各類工廠,為企業提供10美元以下的廉價商品,于是這就構成了企業的“里子”和“面子”,新加坡身份負責“面子”,番禺的小工廠和辛苦勞作的產業工人則成了“里子”;
4)近幾年地緣政治形勢不斷惡化,希音又在此進行一系列“身份套利”行為,2020年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西方國家污蔑中國新疆棉花產區存在強迫勞動,掀起了抵制新疆棉運動,包括H&M在內的企業都參與在內,成為彼時最大的地緣政治事件之一。
為穩定海外市場份額希音在海外表示不會采用新疆棉花(紐約時報曾有報道,見下圖),在中國內部對此則閉口不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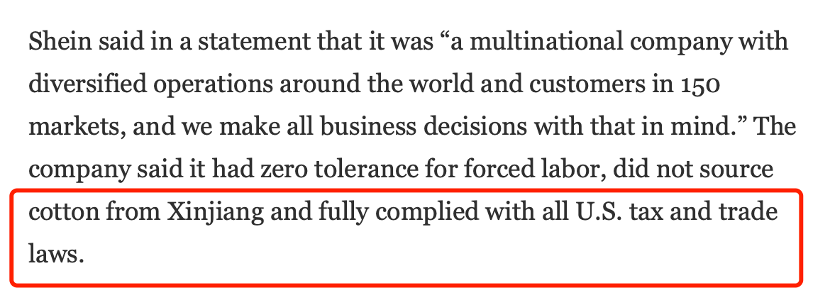
這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操作究竟是為了什么呢?IPO是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根據多方媒體報導,希音要在2024年完成赴美上市(根據彭博社信息,希音在一級市場估值從2022年的1000億美金降到了當前的660億美金,上市意愿極為迫切),在我國監管環境不斷收緊這一背景下,企業往往需要以“監管套利”落實此目標。
中概股境外上市,大都存在把境內運營公司裝到境外上市主體的過程。《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第11條明確規定:境內公司、企業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設立或控制的公司名義并購與其有關聯關系的境內的公司,應報商務部審批(為防止資本借“假外資”外逃)。
從此中國企業家轉換身份變為外籍人士就成了最常規手段,俏江南的張蘭,海底撈的張勇,龍光地產的紀海鵬等企業家都在沖擊IPO前突擊改變國籍,其本質也是為繞開此規定。
此外2023年2月發布的《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又強化了中概企業境外上市的報備機制(第13條“境外發行上市的境內企業,應當依照本辦法向中國證監會備案,報送備案報告、法律意見書等有關材料,真實、準確、完整地說明股東信息等情況”)。
對于估值搜索,背后投資者焦慮越發強烈時,這無疑阻礙了希音的正常上市進程,于是學習前輩們改變身份,實現監管套利。。
既要享受中國高效低成本的制造業紅利,在海外上市時又不想處處受限,就通過“身份套利”來實現“監管套利”,搖身一變從中國企業變為新加坡公司,創始人又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以海外企業完成上市,實現個人財富的收割。
此外避稅問題往往被輿論忽略,我們在此做簡單介紹
對于許仰天來說,新加坡在稅收上有三大吸引力:
1)免收資本利得稅(包括股票買賣和股息,我國雖然免收資本利得稅但征收股息紅利稅);
2)新加坡對居民海外收入免稅,避免了中國新個稅反避稅實施后可能面臨的稅務風險;
3)可通過“移民新加坡”+“離岸家族信托+BVI公司”,將股權全數裝入離岸信托,放棄所有權,只享有受益權(為信托受益人),以此,隔離了家族資產的債務風險。放入信托的股權所有權不再屬于許仰天,股票也已在英美普通法系的保護之下(離岸信托),并最終流回不(對海外收入)征稅的新加坡,實現家族財富傳承。
如此公司和許仰天國籍的變更就加速了IPO的進程,進而實現個人財富的迅速膨脹,選擇新加坡作為新國籍又規避了我國的稅收制度,以避稅方式實現財富的保值。
算計如此之深,此后這一切會按照劇本進行嗎?
西方主流不認希音換國籍
無論是更改國籍抑或是對新疆棉等敏感事件的表態,這些都能感到希音的自我身份焦慮,如開篇我們所言這是一個典型的“既要,又要”思維,衡量其結果能否符合預期就需要判斷究竟外部把希音視為何等國籍公司。

從法律上希音確實已經成為一家新加坡人主導的新加坡公司,企業官網幾乎看不到任何有關中國的信息,這確實可以實現我們前文所分析的IPO和財富利益最大化目的。
但另一方面,我們要考慮“社會共識”是否已經完成了希音的“去中國化”。
美國連線雜志曾發表了一篇《Fast, Cheap, and Out of Control: Inside Shein’s Sudden Rise》的長文(關于希音快速成長的文章),在該文中出現“china”9次,“global”近兩次,且記者前往番禺希音工廠考察產業鏈,尤其觀察工人的工作時長以及碳排放問題。
這基本反饋了西方主流媒體對希音的基本看法:即便企業已經通過一系列操作改變了身份,但“西方共識”并沒有改變其定性,在關鍵問題上依然用中國眼光看待,甚至會更為苛刻,如記者對碳排放問題的觀察力度已經超出了同類企業,希音的潛在風險并沒有消散。
C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亦在2023年10月發表了一篇關于希音長文,其中“China”更是出現了22次之多,文中一方面也認可企業身份變更有利于降低美國方面的地緣政治敏感度,可以一定程度上規避中國方面監管壓力,但另一方面又說明只要企業供應鏈體系依附于中國市場,外界就仍然有理由在當前的地緣政治背景下對其不信任(如敏感的數據安全),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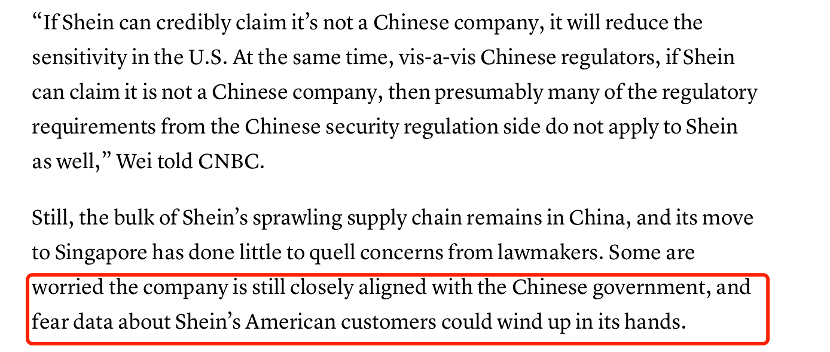
主流觀點對希音一列操作的不認同,就把企業推到了一個尷尬境地:身份已然更改,只能硬著頭皮往前沖,根據CNBC披露企業開始將供應鏈向巴西,土耳其遷移,且正在評估印度和墨西哥市場。
在希音發展之初,中國市場為其提供了勞動力,人力甚至是政策支持,如今企業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準備將產業鏈遷往海外,這與近期富士康在中國市場的一系列操作如出一轍(在享受中國市場紅利后富士康供應鏈向東南亞遷移)。
接下來希音就不得不面對:在海外盡量討好海外主流輿論而不得,在國內又不得不面對供應鏈遷移之后紅利消失的問題。
短期內很難想象,希音離開中國市場的地利優勢之后如何保存其競爭力,尤其在當前的地緣環境下,希音的行為很可能讓其失去政府的支持,面臨當前富士康一樣的處境,這反而會降低成長預期,影響一級和二級市場估值,最終影響財富的膨脹和收割。
分析如此之多,我們對希音的身份焦慮開始有了更多的思考,作為一家“精致利己主義”企業,企業為股東和員工創造財富本無可厚非,只是過多使用身份套利來規避監管套利,很可能實現“皮變而心不變”,在地緣政治中過于善舞長袖很可能會被反噬,這是市場投資者,企業管理者要尤其引起注意的。
隨著上市工作的推進,希音要強化信息披露制度,屆時緘默不言的身份問題就要浮出水面,在一些問題的表態亦要體現在招股書的“風險提示”中,我們很難想象這些信息再傳回中國市場,輿論以及政策端對希音會有怎樣的反饋,企業也應該做好相關應對工作。
1.TMT觀察網遵循行業規范,任何轉載的稿件都會明確標注作者和來源;
2.TMT觀察網的原創文章,請轉載時務必注明文章作者和"來源:TMT觀察網",不尊重原創的行為TMT觀察網或將追究責任;
3.作者投稿可能會經TMT觀察網編輯修改或補充。

